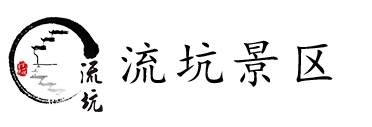流坑的民情风俗--流坑的“玩喜”
发布时间:
2015-03-13 15:35
“玩喜”就是出傩神,跳傩舞。流坑现有36具傩面,又称“戏面”,舞起来十分热闹。1957年时,还参加过抚州地区的文艺演出,在乐安也自称一派。
流坑傩舞的起源已难确定,但乡民们的口碑,则把它与宋代的祖先董敦逸联系起来。故事分为前后两段,先是说董敦逸官拜监察御史,奉钦命赴契丹议和。途中遇一女子,将契丹国情况及风土人情详细告知,使得董敦逸到敌国后,面对各种诘难,可以对答如流,如数家珍。致使契丹国主叹服,同意议和。董居契丹十二年,方才回中原。途径当年遇那女子之处,登门致谢。不料那女子已经亡故,敦逸感叹不已,遂请来艺人,照他回忆的形象,刻成那女子的面像。另外,又把当地的跳傩仪式也带回京城。
跳傩又如何传入流坑的呢?这是故事的下半段。说是董敦逸归朝后,不久即遭奸臣谗言中伤,罢官回家。遂让说书僮董弼挑回一担傩面具,前为“武傩”,后为“文傩”。进赣江后乘船,正遇风浪,一个颠波,把一头的“文傩”打下水中。说也奇怪,这傩面竟逆水而上,忽悠悠一直飘到南丰。乡老们说,闻名全国的南丰傩舞,就是这样从流坑传过去的,而留在流坑的,就是那半担“武傩”。
口碑之“神”,就在于乡民要给自己的许多生活现象和习俗找到一个源头,寻求一种历史的合理性,同时也给流坑的傩确立一个地位。但据一些文化工作者的分类,流坑的傩舞更接近于“文傩”的一类。
1、傩神庙的分布和“戏面”
在流坑,旧有“八房八傩班”的说法。许多房都有自己的神庙,其中一些就是祭傩神。有些傩神,则放在村子周边的敌楼里,归各房管理。口碑能讲述得清楚的,房与庙大致有以下的对应关系:
文晃公房——太子庙
桥西房(含胤功、胤华二枝)——三义庙
镜山公房——五王庙
胤明公房——拱宸门
胤隆公房——启明门
胤昂、胤旋、胤达、坦然四房——里仁门
双桂公房——关门阁(俗名,又称“中流砥柱” )
纯然公房——真江门
村名们说的“傩神”,就是指傩面具。凡有傩面具处,都有“诺神会”组织,实即为出傩活动而设的基金会,有专门的田租收入。从现存碑刻看,胤明公房的这种基金 会组织叫“士心会”。辛亥革命那一年,拱宸门因洪水而墙垣倾圮,傩神像也遭虫蛀。后由“士心会”一批人士出面,“积资重建,乐善好施,以负完全责任,数月告竣”。胤明公房谱记载该房祭傩的由来:
古者岁而时傩,吾乡之奉此神,亦有行古之道也。我先祖立庙北垣,就拱宸门上架造敌楼,中祀炎储、关帝,旁纳诸傩神面。
拱宸门中现存民国碑刻亦称:
村之北为胤明房公支,子孙蕃衍,所居经十余世矣。村口空缺之处,立有敌楼,上塑汉代帝王将相以及傩神等百有余像,祀享血食,惠泽生民。
可见平时傩面具也是挂在庙内(或“门”内),和其他神像一起,享有香火祭拜。乡老们回忆,过去各庙(门)中的傩面具都一种格式,各有三十多个。现在全村惟有完整的一套,放在村委会的楼上,共三十六具,名目如下:
钟馗、天官、灵官、元皇、马元帅、朱元帅、温元帅、哪吒、金刚、魁星、赵公(财神)、小鬼、真武、三官、和合(二仙)、周公、桃花女、书生、七仙女、土地、大和尚、小和尚、走报、刘备、关公、张飞、孔明、赵云、蔡阳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。
这套傩面,是“文革”以后重新刻的,如人面大小。木壁较厚,两耳位置拴绳,演出时戴在脸上,嘴脸全部盖住,故不能出声演唱,全无戏文。傩面着色,有的如常人肤色,例如书生、桃花女、大小和尚、“土地”等。有些则靛脸朱眉,如几个“元帅”就是。“关公”赤面蚕目,“孙悟空”自是猴相,有很重的戏剧色彩。这些都表现出对传统戏剧的某种移植或简化。
2、傩舞的演练与习武功能
有一个面具,就要一个人去“玩”。三十多具傩面,至少要三十多个人来演出。乡民称舞傩者为“傩班”,他们由各房的男人们组成。出傩活动完全是分房进行的,有的房人丁少,凑不齐一个班子,往往请其他房的人来帮忙。
传统的流坑傩舞演练,兼有练习武功的作用。前引胤明房谱即记载了缘由及操练情况:
所由来者,吾族地居谷口,实为闽广山寇经途。扰攘之时,屡遭其害。我先世尝修武备,借戏舞以为训练,内以靖其氛,亦外以御其侮也。然而事虽近戏而周礼不废,似亦未敢厚非。一举而两得,古之人有行之者,吾何为独不然哉?因以纪其事。
每年冬月,子弟操习拳棍团牌。新春月初,结台演戏,装扮古传,成部教演战阵兵法。
将舞傩训练与先世抵御“闽广山寇”的“扰攘”联系起来,似乎是暗示这一习俗的起源不会早于明代中期,因为流坑人记忆最深的一次“闽广山寇”的侵扰,就是嘉靖 四十年(1561)烧毁了大宗祠。从那以后到万历十年(1852)间,流坑人为加强自我防卫的能力,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也许“借戏舞以为训练”,正是其作为修武备,御外侮的备战措施之一。所以这一记载才会把冬季农闲时的子弟操习拳棍团牌,与新春时节排演傩舞,仍需“成部教演战阵兵法”联系起来,“事近戏”则含有增加训练趣味的用意。这段记载是值得重视的,但话并未说得十分透彻。其实,作为一个强宗大族,无论是保护应有之物,还是向外扩展势力,“强悍”是其不可缺少的素质之一。提倡族中子弟习拳脚、练武艺就极其自然了。另外还应看到,流坑人的重要财源来自于放排,卖木材,放排工很多。他们平时是种田人,但一旦放排远行,过的就是水上流动生活。不仅要与水斗,还要预备和沿河的人斗,才可免受欺负,保护自身的安全。所以我们还了解到,过去流坑出了一批武艺出众的“打师”。
然而,傩舞毕竟是一种集体性的演出行为,是要排练的。“傩”是赶鬼驱疫之舞,具有一种神性。平时是普通族人,一旦戴上傩面,出现在众人面前,即有一种特殊的庄严气氛,讲究一套程序和身段、步法。所以到民国时期,各房的规矩还是每年腊月二十四日开始,由老者一出一出的指点进行,前后约一周时间。近年来,虽然流坑还出傩,但谙熟前后场次的老人已经少见,也只有一个傩神班出游。
3、傩舞的演出和艺术特色
民国五年,胤明房“出傩”的简单过程是:
凡房下喜庆,俱得籍以致贺。元宵装扮神像,扫荡街巷。是夜汛扫庙楼龛座,中夜房长率众行四礼拜,祝圣安位。即将经年竹屑杂秽着送至楼下塘塍上焚化,回身复行四礼拜,关闭宫寝如常。
看得出,这一记载的重点,在于正月十五(元宵)夜“出傩”与“收傩”情况。所谓“装扮神像,扫荡街巷”,即古代社会中“执戈扬盾”,以傩驱鬼逐疫仪式的表现。实际上,在每年正月里,从初二起,各房“傩神”都是要首先出游一次的,走遍全村,由此而宣告一年一度的出傩活动开始。而在元宵夜,出傩达到高潮,也是尾声,因而当夜要清扫傩神龛座,并将庙(门)中一年积淀的垃圾秽物(可能还包括出傩后废弃的抬杆、火把等)送去外面烧掉。然后,将出游回来的傩神放归原位。房长在仪式中起司仪作用,都要行跪拜大礼,最后以“关闭宫寝如常”而结束这一年的出傩活动。
另据回忆,民国年间出傩和收傩之日,不仅有仪式,还要由年轮值的“神首”去请道士。道士持有一枚薄木板刻的印章,上面刻满了小船和小人。道士先念咒语,然后手拿卜吉凶的“神珓”一副,离地约二寸,顺手滑下去,一般必得三个“顺珓”,这才可取下舟画去焚烧。焚舟画又称“送顺”,标志着出傩结束,送神明上天,故各房操持事务的管首们都必须在场。焚毕,停锣息鼓。返回庙中,跪拜。然后吃一餐“神粥”,散去,全部仪式宣告结束。
但村民印象最深的,是傩面的“玩喜”功能。这一点,充分体现了流坑傩舞“娱人性”的一面。
“玩喜”,要从有喜庆之事的人家说起。每年正月初二起,直到正月十四日,凡在头一年有中举、生男孩(所谓“添丁”)、娶媳妇、“接郎崽”(即嫁女)等等喜事的人家,先派小孩去本房的傩神庙中,请来傩神,抬回家中。此间先有一个“走报”来到门口,大声报喜。如果是娶亲之喜,“走报”即送上一个泥娃娃,祝其早生贵子。“接郎崽”,就送一副“指日高升”对联。中举、毕业者,对联上写的就是“状元及第”之类的祝词。
然后迎进傩班,在家里的厅堂作一番表演。此间,要将傩面供在香案上,焚香,燃放鞭炮,上供品。祭拜一个时辰以上,然后抬到村中的戏台上去。
傩面到了戏台,乐师等也陆续携带乐器赶到,做好准备。先由神首焚香点烛,燃放鞭炮,并高声报出喜庆人家的姓名和喜事。接着,傩舞的表演开始了。演出的剧目有:
“钟馗扫台”、“天官赐福”、“出将”(出黄灵官、马元帅、温元帅、元皇、哪吒、金刚等)、“出真武”、“出三官”、“出和合”、“周公与桃花女”、“安庙装香”、“闯辕门”、“斩蔡阳”、“取经”等。每出剧目,都突出了某一个傩神的中心地位,有不少的明显吸收了戏剧的内容,故事性强,也很讲究服饰。文蟒武靠,云绢彩衣,色泽鲜艳。动作舒展平稳,脚步深沉有力。因为只跳而不开口唱,所以演出犹如一部连本哑剧,富有情趣。
傩舞不唱,但有音乐伴奏。伴奏又有文场、武场之别:“文场”有二胡、笛子、大唢呐、小唢呐等。“武场”则为全套打击乐,有鼓、锣、钹、大锣、铃、木鱼等。曲牌有高雅浑厚的《风入松》、《浪淘沙》,也有《小桃红》、《刮骨令》、《水底鱼》、《麻婆子》等。还有活泼的民间小调,如《五更恋郎》等。都是根据剧情、场景与情绪的变化而变化,婉转动听,表现力强。在全乐安县,流坑“玩喜”的乐队最为出色。据口碑流传,这是因为明代后期,招携一枝的族人董裕任南京刑部尚书时,曾带族人中子弟去宫廷乐队学习过,以后一代代流传下来。
最后一个节目称“抢罗汉”。此时全部演员都取下面具,一起登台演艺,打拳、踢腿、翻斤斗、跳桌子,随心所欲,各逞其能。但依然是只有动作,没有戏文。可想此时台上台下,充满激情,喝彩欢声,把演出推向高潮。在民国时期,全台戏演完,前后要用四五个小时,所以一般上下午各演一场。演出后,遂由喜庆之家请酒吃饭,一般都要五到六桌款待众人。如果有喜之家实在贫困,请不起酒席,就包一个红包送到庙上(或“门”),称为“喜钱”。钱数多少不拘,聊表心意。因而请人“玩喜”、吃饭等,又被称为“还喜愿”。
民国期间,流坑固定的戏台有三个:一个仰山庙前,一在太子庙前,一在五王庙前。如果某年有喜事的人家多,戏台不够用,就要先期搭临时戏台。由此也可推知,“玩喜”的场地和场次,应该是事先有所安排的。
本来各色恐怖狰狞的傩面,被流坑人用来志喜,也为求得保护。
4、“行靖”与“吞头”
正常年景,出傩游神,“玩喜”致庆。遇有大疫灾异之年,则要举行“搜傩”仪式。在流坑,称“搜傩”为“行靖”,仍有口碑可证其事。
流坑的老人,只记得见过民国三十四年的那次“行靖”。那年,天灾严重,五谷不登封。更可怕的是疫病流行,青壮年连死多人。由是人心惶惶,盛传是瘟疫降临,唯有借神以逐鬼驱疫。于是先由各房长老们进行筹划,请来道士,设道场禳灾。到了规定的那天夜晚,几百村民出动,分成两批行事:大多数人,用劈开的毛竹夹上油柴,点着,插遍大街小巷,然后开始大扫除。另外拣选了十几个青壮年,身穿铠甲,手执各种兵器,戴上狰狞可饰的面具,犹如天神一般,走街串巷。在他们身边,还有身着常服的助威人员,手拿铁叉、竹筲等器械,并提灯笼和稻草火把,横扫各条街巷,穿户入室。与此同时,锣鼓齐鸣,鞭炮顿起,全体人员大声喧喝呐喊,作驱鬼状。霎时间全村就像开了锅一样,亮如白昼,呼嚣之声此起彼伏,且带着一种原始的凄厉,令人不寒而栗。又如战场,有着十分的气势。结果,这样连续三个夜晚,“行靖”才算结束,花费了上万块钱。老人们追述此事时,留下一个疑惑的结尾:即“行靖”以后,疫病确实消除了,人畜转危为安。老人们推测,也许这么多人出动,毕竟是彻底地搞了几次大扫除。加上到处是火把,对空气消毒,杀害有害的病菌,都可能有作用。也许,心理作用也是应该考虑的,既然已经“行靖”,人神共怒,妖疫如何不会驱走?所以自然增 强了抗病的自信心。精神一振奋,人体的抗病能力也得到激发和调动。
由傩面的赶鬼驱疫,又可联系到遍布流坑房宅之上的“吞头”——村民房宅上的镇宅兽头具,一种用以辟邪的神物。
在江南不少地区,乡村民宅大门上方的辟邪兽头称为“吞口”或“天口”。流坑村民则称之为“吞口”,在族谱中,有的还称为“吞布马口”,原义不详。按传统的风水理论,民居可分吉宅与凶宅两类,而在建房时,都尽量测好风水,选好地基,以趋吉避凶。但如果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,无法随意选择时,就必须借助守护神的威力,在门口挂起“吞头”来驱邪止煞,逢凶化吉。不过,在流坑村内的各条街巷,有此神物与无此神物的房宅,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异向或差别。据介绍,“吞头”实物,旧时全村触目皆是,只是到“文革”期间才毁去多数。可见后来挂“吞头”,已不是一种应需的不得已举动,而是一种非常普及的吉祥物了。
相关新闻
在线客服